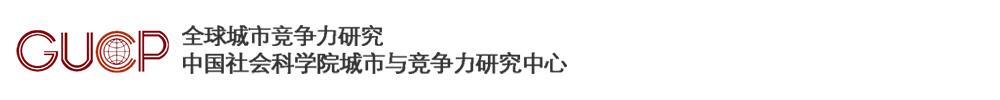周大鸣:人类学一定会在中国扎根
(周大鸣教授在中山大学马丁堂接受了徐杰舜教授的采访。本文是黄锦根据录音整理而成,并经周大鸣教授审阅修改。)
徐杰舜教授( 以下简称徐) : 周教授,非常荣幸能够对你进行第二次专访。我们的第一次专访是20 世纪 90 年代末,在南宁的西园饭店的宾馆里,我们谈到中国人类学的一些情况和未来发展的一些可能的走向。就当时来讲,中国的人类学开始进入一个比较好的态势,很多的学者从国外回来,你当时也是第二次访问美国归来。那么,十多年过去了,我觉得周教授在中国人类学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有很大的贡献。我想,读者们也很想了解,中国的人类学家们,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有些什么新的变化。因此,我现在开始了一个新的计划,就是重访,从人类学的回访中学到的,10 年或者 12 年后重访为中国人类学作出巨大贡献的学者。今天就趁这个机会,对你进行第二次的专访。首先,我比较感兴趣的问题,也是读者们非常想了解的,就是周教授这十几年来的学术成果,能不能够给我们概述一下?
周大鸣教授( 以下简称周) : 这十几年来,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单位以及国家,都是变化很快的一个时期。那么,这 10 年我个人跟以前相比,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做了一些组织工作,主要是组织了研究团队,做了一些事情。2000 年,我开始接管人类学系,刚好赶上国家评选重点学科,我们拿到了国家重点学科,也就赶上了国家重点资助的潮流。像“211 工程”、“985 工程”我们都在做,所以,也就有比较多的钱来组织学术研究、学术交流以及各种各样的活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作为发起单位,已经召开过多次国际大型会议,最多一次有六百多人参加。第二就是进行了系列的研究,10 年来我们大概出版了几十本著作。
徐:有哪几个系列?
周: 一个是中山大学人类学文库,还有中山大学人类学民族学文丛、中国田野调查丛书和中山大学人类学考古学译丛 4 个系列。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教学、科研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从本科到博士后的教学方案、课程设置以及学术定位,我们都做过充分地讨论。这十几年,系里一直坚持以社会调查为基础的学术研究,从本科、硕士到博士,要求所有的学生都将田野调查作为最基本的训练,如果没有做过田野调查就不能拿到学位。另外,我们也动员社会力量,成立了中国田野调查基金、马丁堂田野调查基金,鼓励、引导学生来做田野调查。从我个人来讲,在应用方面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参与了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还有国务院部委和政府部门的一些项目,这对整个应用人类学的发展也是很有影响的,把一个纯粹的书斋性的研究推向应用研究。
徐: 根据你的概述,我觉得有三个问题值得你进行比较具体的介绍。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所说的,人类学走出书斋、走向社会成为一种应用学科;同时,在应用当中人类学得到了普及,获得公众的认同。我记得你在光明日报发表过一篇《中国人类学的应用性格》,能不能结合世界银行贷款项目评估,对这个问题稍加介绍?
周: 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的社会评估,实际上是世界银行在多年发展过程中总结经验教训,结合人类学、社会学方法形成的一套评价体系。过去,世界银行做项目,只做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的评估,着重在经济和技术方面。但这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就会遇到很多问题,项目往往达不到原有的目的。因此,世界银行就增加了两项评估: 一个是环境评估,一个是社会评估,对每一个投资项目可能引起社会影响做出一个评价。比如说,投资可能引起当地社会结构的变化、贫富分化,有的既得利益者可能获得比较快的发展,也有可能导致项目区与周边区的结构性差别,另外所选择的项目不是当地人需要的,或者实施的方法不是当地人可以接受的。又如,涉及到大规模的移民,也要做出相应的社会评价,而且这在世行评估中都是非常严格的,称作“零忍耐”政策,就是说只要社会评价不能通过,项目就不能上。所以,社会评估对一个项目有着决定权,我们所做的评估报告都要在网上公开,要经得起社会各界的检验和咨询。
徐: 能不能举一个例子? 就是在你们的评估当中没有上的,或是经过你们的评估,最终没有得以实施的项目。
周: 评估完了之后没有上的项目也不少,项目资金有可能会转投到别的地方去。因为每年国家发改委与世界银行有一个计划,要完成多少在中国的贷款。中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东部沿海地区吸收资金的能力强,不管有什么项目都有办法拿下来; 反而是西部,一些贫困的地方形成项目的能力差,而往往这些地方的社会评估问题就比较多。后来我发现这个问题,就不再是仅仅否决项目,因为否决以后资金又会流到沿海,那还不如提一些建议,建议怎么改进。有时候一个项目要改进,需要做很多次的反复。比如说,本来计划在西部 4 个省区做一个“绵羊与西部发展计划”,开始是想用澳大利亚的绵羊来替代国产羊毛品质不好的羊。但在实际调查过程中发现,绵羊所适应的生态环境是有条件的。对于西部高寒地带,我们一开始以为澳洲绵羊毛那么厚应该是不怕冷的,后来发现在高寒地带绵羊没有山羊的生命力强,一是不耐寒,再一个就是吃草的能力、自我取食的能力没有本地羊那么强。此外,有的地方本身就不愿意养羊,更愿意养牛,比如说陕西有秦川牛的传统项目,卖得很好,养牛又有经验,而养羊本身有一个问题就是对生态、植被破坏太大。而在新疆,他们不养牛不养羊,养马。最后,经过反复调研,我们就将项目重点改成多样化,让项目区自己来选择养殖品种,设计的项目改题为“畜牧业与西部的发展”。
徐: 我去过澳大利亚,澳羊的生长环境与国内羊的环境完全不一样,真的不能在高寒地带养殖。
周: 澳羊主要以圈养为主,很少像我国这样放养,所以很多东西还是要去了解当地人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
徐: 在做世行项目评估当中,你可以说很充分地运用到了人类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刚刚所讲到的例子,体现出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另一个还体现出文化的多样性。这样最终改变了项目的方向,发展畜牧业。你和你的团队应该说是对人类学在中国的应用做了开拓性的工作,希望你在这一方面多做一些总结,现在已经有这方面的总结了吗?
周: 出了两本书,一本是《参与式社会评估: 在倾听中求得决策》,还有一本是《寻求内源发展——中国西部的民族文化》,把这些年做的应用性项目做了一个总结。另外,我现在还参与一些政府组织的工作,近两年一直在做广东省社会发展指标的评估。过去的社会发展指标的评估只做定量,没有定性。单纯的定量分析就是总结统计数据,得出的结论与一般的常识不太一样,所以,政府部门决定还是要做定性的研究。
徐: 从你刚刚讲的社会评估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有很多人类学的理念在里面。但是怎样把这些提炼出来,这个我们留着以后做再进一步的探讨,可以写出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出来。我想问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人力资源方面的。在你领导人类学系的过程中,引进了一批优秀的国内外的人类学博士,你的这个想法和做法能不能向大家介绍一下?
周: 我觉得一支教师队伍,特别是在一个好的学校,教师队伍一定是多元的。如果你到哪个学校,那里的老师在一起说方言,那一定不是一个一流的大学,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看法。像哈佛那些一流的大学,都是各种族群的人在一起,比较讲究多元化,这个多元化我觉得就是民族的多元化,还有一个就是来源的多元化。这对学生是有好处的,学生会听到一些不同教育背景的人传授知识。有时候完全是一个师傅培养出来的人,对学生不太好。另外,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会考虑对中国比较有了解的人,有的人在海外留学后会对中国很陌生,回国内很难适应。所以,我们还要看他研究的课题。我们一般会请他先来做一个讲座,这其实就是对他进行一个考试,感兴趣的老师都会来听。第二方面,就是要满足我们的制度要求,现在的制度对学历的要求很高。像我当系主任的时候,整个系也就我和刘昭瑞两个博士。后面引进的人都有博士学位。凡是留在校内的、准备在学校里干下去的,全部去读在职博士。对这部分教师,我就从经费里给每个人 10000 元做论文,这个在当时是很不错的。经过几年努力,我们系 90%的人都有博士学位,整个教师的学历结构改变了。说实话,去拿博士学位,有一个写博士论文的过程,这对以后训练学生是有帮助的,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形式。
徐: 就人力资源这一块来讲,你的教师队伍的结构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在你当系主任期间,你从哪些国家和地区引进了教师?
周: 主要是日本、美国、英国和香港,还有一个德国教授。
徐: 所以你这里的师资队伍,从你开始当系主任到现在,就给中大的人类学系建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人力资源结构。与别的学校相比,它反映出来的就是你这里的成果确实是比较多的。我觉得现在你们的书都不知道出了多少了?
周: 我也没有好好统计过,现在我正要学生在做这方面的统计。
徐: 还有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你培养了一大批博士,现在已经有三十多人毕业。这批博士在全国各地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能不能谈谈对培养博士有些什么样的体验?
周: 其实培养博士,我当时也是想多样化,不同民族的学生都招,有藏族、撒拉族、蒙古族、回族、壮族、侗族、白族,等等。还有就是招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有不同的学术背景,我也不太愿意全部只招来源于同一个地方的学生。所以我招的学生,本身中山大学毕业的并不算太多。
徐: 你对博士的培养,为人类学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人力基础。我到新疆、青海、四川、云南,都有你的学生,都在当地成为教学、科研上的骨干、行政上的骨干,这也应该是你几年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成绩。你培养博士生的经验呢,我还是觉得你能够进一步地总结,以后这些培养的经验还可以适当地做一些交流。
周: 博士培养我们整个系一直向制度化发展,比如在招生中,我们是集体出题,不是个人出题,谁出题是要保密的。面试也都是先集体出好题,一半要抽签,一半问问题。从预答辩到答辩,我们也要允许答辩的委员有不同的声音,像马戎、陈庆德是比较严厉的,我们每次都请这些要求严格的老师参加。提意见会对我们的学生有冲击力,低年级的学生也会听到,对他们的论文写作会有帮助。中山大学对博士论文每年都要抽查,请校外专家匿名评审。校长还会与抽查不合格的导师进行“问责谈话”,一般都要停止招生。而我们系的论文抽查还没有出过问题,基本上是全优,这个非常不容易,这说明我们博士培养的质量还是可以的。所以,在制度化方面还是积累了一些东西,我们希望通过制度,而不完全是导师个人化的东西。
徐: 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是你很有创意地在国外办英文版的刊物,这在国内也很少有人能做得到。据了解,你现在有两个刊物,第三个刊物也在筹办中。能不能把你在国外办的相关刊物的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
周: 首先,一个原因就是在国内办刊物拿不到刊号,迫使我们到国外去办刊物。第二刺激我的是,现在英语语言的霸权太厉害了。在国外几乎做中国研究的人不阅读中文文献。当然也有例外,做中国历史的学者要阅读中文文献。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用英文发表的文章,人家根本就不看、不引用你的东西。所以,我强调首先要做出东西来再去跟人家对话,而要对话关键就是语言问题。我希望把国内同行的研究介绍到国外,我都是一组一组地组织文章,每一组文章就是在中国的某一项研究,比如说,像做藏区的、城市化的、城市性别的、艾滋病的、回访的,每一组都有一个主题,把中国在人类学、社会学这些方面的一些重要的研究介绍出去,增加国外的同行对我们的了解,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从人数上来讲,中国是世界上做社会科学研究人数最多的,但是因为语言的限制,阻碍了国外对我们中国研究的了解。所以很多东西都有误区,认为我们是共产国家、专制国家,没有什么民主,这都是被那些在海外懂一些英文、反政府的人的少量文章给掩盖了,包括藏学研究和新疆研究,都是这样的。有一些搞藏独的、疆独的,他们在国外拿的学位,文章都是英文发表的,影响比国内的要大。无论从政治的影响,还是学术的影响,在国外办刊物都是很重要的。要让国外的学者了解中国学者的研究动态。另外,也是一个制度性的原因。现在我们国内的考核都要什么SSCI、SCI,如果不用英文发表,很难进入这个系统,在中国只有少量刊物进入了这个系统。而就算你进入了这个系统,还要看引用率。现在作为大学的一个指标排名,要看 SSCI、SCI 文章的多少,要看影响因子多少。现在各个学校都意识到了用英文在海外刊物上发表文章的重要性,因为现在这个被引用率变成论文的排名,决定了学校的排名,这也是一个制度的导向所造成的。到国外办刊物变成了赶热潮,迎合了这个时代的发展。
徐: 第一次办刊物是 Chinese Sociology andAnthropology(《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 。
周: 对,第一次接触刊物是很偶然的,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已经办了有 50 年了,我最初是做客座主编。后来做主编,我担任主编的第一期,他们还专门发了一个消息,说这是第一次请大陆的一个学者来做主编,这些年就一直做下来了。然后是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thropology(《国际工商人类学杂志》) ,是我和朋友田广一起主办的。田广在国外做工商人类学,在美国出版了一本《工商人类学》的书。工商人类学在人类学应用方面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田博士想看看能不能与我们中山大学合作培养这方面的研究生。我想,人类学和工商如果能够结合的话可能也会是一个新的方向。我们现在都是按照国际刊物的那套制度,评审按照 SSCI 刊物所要求的那些表格,包括匿名评审,我们也都是这样做的。现在我们已经出了第三期,我们想出到第四期就开始申请 SSCI。等第二个刊物进入 SSCI 之后,我准备再办第三个刊物。
徐: 第三个想办什么?
周: 第三个名字已经想好了,叫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of China( 《当代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 ,我还是想等第二个刊物办得成熟一点再办第三个,这个学校已经答应经费支持。
徐: 这真的是很有远见。因为中文的东西人家读起来很难,现在虽然世界上掀起了汉语热,但是为了做生意,它还没有发展到学者们都要来读中文的东西。
周: 前一阵子,我们还和台湾、香港的大学合作,准备办一个应用人类学的刊物,也是想要用中英文双语。这是不约而同的,两岸三地都有这样共同的愿望来办这样的刊物。
徐: 所以我们中国的声音,真的要通过英文这一工具来表达。
周: 这个没办法,不得已而为之。很多人就是说,为什么要去迎合西方? 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里,我刚刚讲的,在政治上,几篇藏独、疆独倾向的文章,国外的学者就会引用。要妥善处理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需要人类学家的大力参与,我们有责任把国内主流的研究介绍出去。
徐: 这个工作很具有战略性,有战略的眼光。
周: 我想在未来的几年,我可能会把主要的精力花在做这个事情上面。以前是“西学东进”,我们现在要“东学西进”。
徐: 非常有远见。所以从这三个方面来看,说实在的,中大人类学在你的领导之下,有了很大的成效,在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上来讲,你们大踏步地前进了。回到我们前面要讲的那个问题,人类学要有地位,必须要有作为。最近国家学位办公布了一个新的学位目录,我想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周: 在国际上,人类学早已成为独立的学科体系,具备了一大批具有共同研究规范和价值取向的学术团体、培养人才的学科建制。在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以及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常春藤名校,人类学都是排名靠前的传统优势学科。从 20 世纪初人类学传入中国算起,人类学在我国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形成了独特的学术传统和深厚的学术积淀。改革开放以来,人类学学科分支学科迅速发展,为全国培养了大量各类人才,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科研成果,社会影响力日益增加。人类学在我国的发展已经相对成熟,可以说,达到了成为一级学科的条件。现在,社会学、民族学都已成为一级学科,唯独人类学学科的合理地位一直没有实现,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对这个事情我们原来就有两手准备: 一个是人类学成为一级学科的准备,一个是不成为一级学科的准备。在学科建设方面,我们原来就有准备,过去我们在人类学以外又申请了一个民族学的博士点,大家不理解为什么。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民族学的博士点,我们才有资格申请一级学科授予权,这样我们从学科建设上来讲,我们已经有了一级学科授予权。当然,人类学有一级学科是最好的,没有的话,我们就在民族学学科下面还是可以做人类学的研究,在南方办一个有人类学特色的民族学也没有什么不好。在美国,民族学就是文化人类学,这个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我们在翻译的时候翻成“文化人类学”,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觉得还要继续奋斗,让人类学成为一级学科,而在此之前,我们还是要在制度范围内继续做。不能因为国家学位目录的变化,我们就不继续研究。
徐: 这一点非常重要。人类学在 20 世纪50 年代和社会学、心理学一起,被当做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学科被取消了,好不容易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被恢复。我觉得这一点费老先生的看法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周: 其实当时费老提出这个建议大家没有接受,就是社会学、民族学与人类学三科并立,共同发展。三门学科一起发展,多好啊! 费老是有眼光的人,知道一个学科地位与资源配置的重要性。
徐: 新的这种目录实际上是把人类学进一步地边缘化了。这对人类学的发展是会有一定不利,但是我觉得和你刚刚讲的,不灰心,不气馁,在民族学框架下面我们照样做人类学。在这个问题上,你有什么新的想法没有,能不能说一下?
周: 学科目录的调整对学科建设肯定会有比较大的影响,主要影响到各个学校在人力资源的配置方面。因为人类学要是成为一级学科,各个学校的师资需求会大很多; 民族学成为一级学科,就可能是反过来。所以,我们现在准备把体量做大。考古学方面,我们准备建实验室,建立考古长期的发掘基地; 人类学方面,我们也想要建实验室。这是我们第一个想要做的。第二个就是要为下一步争取国家重点学科做准备,寻求制度下的进一步发展。你的学科发展得越强,你的资金来源,你的各方资源就都能跟上。另外,从学科的研究上来讲,我们可能会把视野扩大,过去做珠江流域,现在要把视野扩大到环南中国海的研究。下一步从研究上来讲,我们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战略转移,除了继续做的研究以外,这是一个研究的重点区域。然后每一个学科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有特色的学科,比如说,我们会集中在都市研究上,因为未来 70% 的人口会聚集在都市,所以,都市民族的研究、城市考古的研究,还有城市族群的研究、境外族群的研究都在开展。这将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转向,就是要把研究向城市集中,包括像人类学传统的亲属制度、城市的家庭、社会的组织、邻里关系、社区的建设,这些都会结合起来。把多个学科结合来做城市的研究,也是我们未来 10年的一个想法。我们现在在做未来 10 年发展规划,这也是和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包括城市的移民联系在一起,未来的研究区域大概就在这几个方面。
徐: 这个规划很宏大,而且也很时代,这是转型,人类学也好,民族学也好,向都市集中,向南中国海延伸则对你们所处的位置来讲非常的适合。
周: 包括少数民族也在进入城市,现在有 56 个民族的城市越来越多了,如果还把传统的民族学放在西部,不进入到城市的话,我们的研究也将滞后于时代。像法律法规、政策,怎么样来适应这种新的变化,城市里面的少数民族怎么样来管理,他们怎么享受他们的权利? 这些都是需要有基础研究的。未来的话,我想也是我们的传统优势,在都市人类学传统的基础上我们的学科优势再继续往下走。
徐: 可以说这 10 年是你的一个发展期,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期。无论是在教学方面、科研方面、应用方面、行政方面,都做得很好。我觉得今后的 10 年可能是你的成熟期,你有这么丰富的经验,有积累的多方面的资料,后续的工作需要进一步去提升,变成经验性和理论性兼具的成果。所以,我觉得今后的10 年对于你来讲,会有更多的收获,更多的成果,更多的学生被培养出来。今后的成果就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个案、田野调查,这一块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些理论升华的思考,像研究生的培养、博士生的培养,都可以进行交流和总结,让大家能够分享你的收获,分享你的成果。
周: 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好多时候没有时间来好好总结消化。我们这个时代大家都有“肠胃病”,消化不良。拿了很多资料,做了很多调查,当你还没能好好思考的时候又得往前走了,这真的是一个问题。刚刚讲到,现在面对未来又要转型,我们未来要向城市里发展,从招学生、编教材、上课,都要往这方面转型,很多东西要读,很多东西要看,很多东西要消化。我觉得我们大家还是在做事情的,我一直跟你就是这样一个态度,我们尽量少讲空话,多做事情。
徐: 总之,衷心地希望周教授继续带领我们南方的学者们前进。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